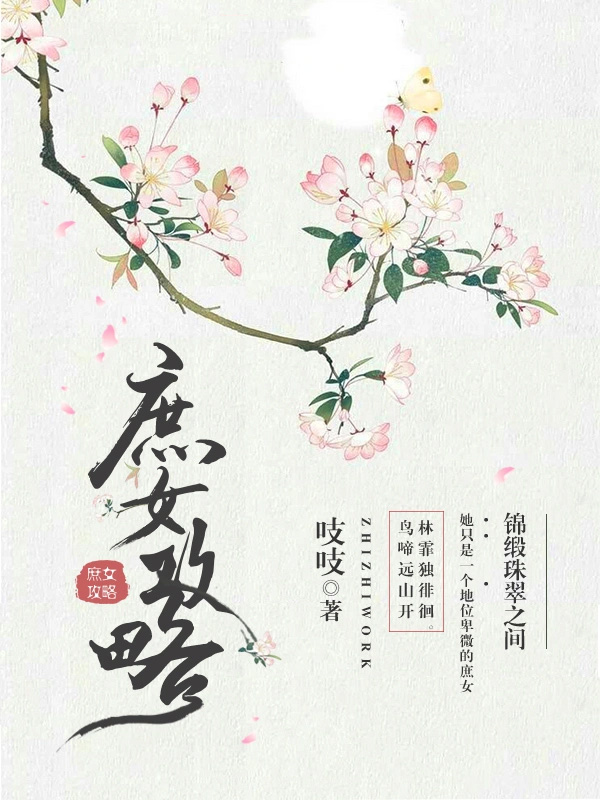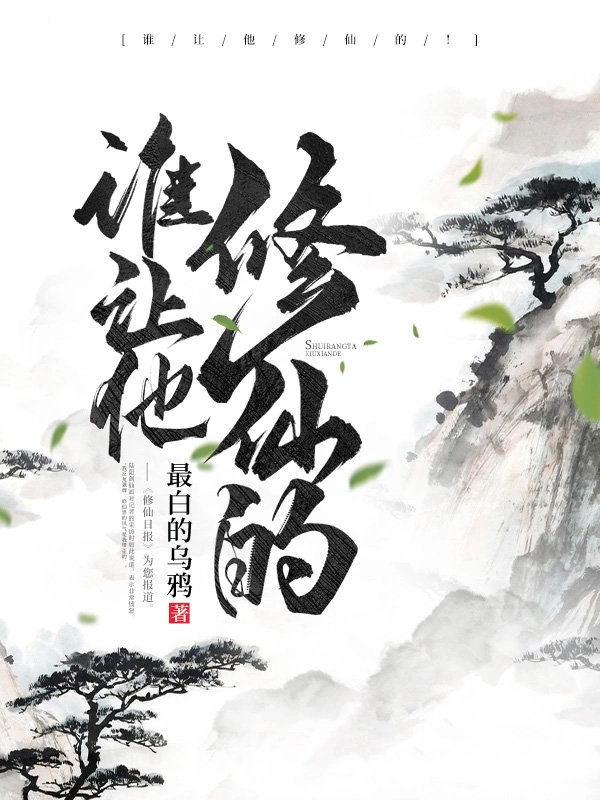第五百零四章 莫名熟悉的字迹
公家的馬車稱不上多豪華精良,但長處在于帶了衙門特有的徽記。
一路上都十分安穩,哪怕是一些想趁着局勢尚不安穩,渾水摸魚的地痞無賴,都避之唯恐不及。
途經長纓街一帶的時候,宋玉枝撩開車簾,仔細看了一圈。
這處昔日最是繁華的地帶,如今卻看着最是可憐。
縱火、搶掠的痕迹十分惹眼,屢見不鮮。
尤其是吉祥、如意這樣叫得出名号的老牌酒樓,更成了重點關照對象。
就跟魏宅一樣,别說裡頭了,就是外頭的門闆都教人拆走了。
宋記的境況隻能算略好一些,不值錢的門闆沒人要,也沒有被火燒的痕迹,但是大門讓人劈開了,不知道丢了多少東西。還有那堵把鋪子一樓隔成兩個鋪面的承重牆,瞧着損毀嚴重。
宋玉枝尤記得當時租賃的時候,主家就說過那堵牆至關緊要,不能拆除,拆了說不定哪天整個二樓都會坍塌下來。
現在宋玉枝隻慶幸自家鋪子是租賃來的,這種不可抗力的損失不用自己承擔。
而那些值錢的物資,又都提前轉移走了。
不然至少損失三分之一的家當,甚至為了修葺鋪面,前頭半年都要白幹。
至于往後……
往後宋玉枝想着先陪着沈遇,去尋訪那位避世的老大夫,給沈遇穩住了傷勢,再做下一步打算,看看是另外選址,重建豐州城内的宋記,還是索性直接去往她向往已久的京城,在京城重立門戶。
她兀自想着事兒,馬車便已經停到了衙門官署。
宋玉枝來過好幾趟了,下了馬車後就準備往偏門去。
劉文書伸手虛虛把宋玉枝攔住了,“小娘子,你家的戶籍文書已經蓋過大印,現今你人又到場,不必急于一時,還請小娘子先行去往霍大人的書房。”
說着話,劉文書就做了個“請”的手勢,帶宋玉枝往正門進。
這種體驗對宋玉枝來說還挺新奇的,畢竟過去的大楚朝有規定,官署裡除開公家人和身上有功名的,其餘人等一律隻得走偏門。
哪怕是人命關天,哪怕是大案要案的苦主,都得從偏門走。
更遑論尋常來辦手續的普通人,都得在窄小的偏門,排隊等候過一程子。
也不知道今日是得了優待,還是朝廷頒布了新的诏令。
劉文書從宋玉枝的神情中,捕捉到了一絲疑問,就解釋道:“小娘子或許猜着了?朝廷頒布了一系列的新诏令,其中就有一條,往後凡是大……大乾百姓,來往衙門都可以走正門。”
宋玉枝就是普通百姓,日常關心的無非就是生活中的柴米油鹽,衣食住行上的小事。
新朝能頒布這種惠及民生的诏令,明顯就比前朝更注重百姓,對宋玉枝來說自然是好消息。
她點了點頭,臉上也多了一點笑意。
見宋玉枝對新诏令有興趣,去往書房的路上,劉文書便多說了幾句。
例如舊朝臨時頒布的那條催婚令,新朝就已經廢除了,女子十七之後仍然嫁娶自由,不會被官府強行配人。
還有稅收方面,新朝也有意向做出改革。
改革之後,像宋記之前那種收益狀況的商戶,就不用承擔那樣高額的稅款了。
不過稅收乃是國之根本,所以現在隻放出風來,還未曾下達确切的诏令。
“方才途徑長纓街,我觀小娘子目光多有停留。那處損毀确實嚴重,修葺和重建少說得花上數月時間。若是小娘子不準備留在豐州城了,不妨還回原籍。若是有關商稅的新诏令頒布,京城自然是第一個受惠的地方……”
便是劉文書不提,宋玉枝也确實有這樣的打算,但劉文書特特說了,宋玉枝少不得要道一聲謝,謝過他的提醒。
劉文書忙讓宋玉枝不必客氣,“且不說小娘子本事過人,看着就非池中物。隻說你夫婿先前為我們豐州城将士和百姓做的事,劉某這些提醒便不值一提。”
說着話,劉文書将宋玉枝送到了書房外。
霍知州尚在忙别的事,還未曾得空過來,隻說讓宋玉枝進去等候。
另外桌上還有書信,是給宋玉枝的,讓她邊看邊等。
宋玉枝再次同劉文書道謝,目送他走遠後,獨自跨進書房。
霍知州素來儉省,用福福昔日的話說,那就是對衣食住行半點不講究。
他設在衙門裡的書房簡單的甚至有些樸素,裡頭隻有一套桌椅,一張軟榻,一條書案,以及一些個裝滿了書的書架,堆滿了公文的博古架,并不見任何奇珍異玩。
宋玉枝掃過一眼後,就收回視線,在靠近門口的圓凳上坐定。
桌上擺着一封厚厚的書信,信封上寫着宋玉枝親啟。
那字迹宋玉枝還算熟悉,從前在宋知遠帶回來的字帖上見過,正是魏先生的手筆。
既然是寫給自己的,霍知州又說了她可以先看。
宋玉枝便立刻展信看起來。
書信裡頭是魏老太太的口吻,她老人家先在信裡問候宋玉枝,說不知道她過得好不好,又說了他們一家去往萊州府後的經曆。
說完那些,魏老太太表達了濃重的歉意,既是歉疚沒在戰亂時給宋玉枝最周全的安排和保護,又說起魏先生月前已得到了新朝的調令——
魏先生重新被啟用,還升了職位,擔任戶部尚書一職。
新朝正是用人之際,定下的上任時間十分緊迫,他們一家索性就不回豐州城了,先同魏先生回京上任。
再相見,不知道是哪年哪月。
後頭書信中的口吻換成了魏夫人。
魏夫人道出了京城魏宅的地址,讓宋玉枝如果願意去京城的話,就回信過去,魏家使人來接,還說不管宋玉枝去不去,他們也會像在豐州城這般,灑掃出一個單獨的院子,給宋玉枝留着,方便她随時去住。
一封書信足足寫了八張紙,差點就裝不進普通的信封。
魏先生大概也是考慮到了這點,輪到他“說話”的時候,他就沒有另起一張,隻把字體變小,縮在末尾寫了幾行,交代叮咛了宋玉枝一番,還提到宋知遠不能荒廢學業……
每一個字,都透着魏家人真心實意地關切之情。
宋玉枝心中熨帖,甚至能腦補出魏家人說話時的口吻。
她一連把八張紙看了兩遍,确保沒有任何疏漏,才原樣把紙疊好,塞回信封。
也就在她整理好這封信的時候,宋玉枝才發現底下還有一封。
第二封書信的信封更小一些,也更薄,又被壓在那厚實的魏家書信下頭,這才沒被宋玉枝第一時間發現。
信封上頭隻一個“宋”字。
宋玉枝确定自己沒見過這字迹——畢竟平頭百姓中,會寫字的人是絕少數,即便是她,接觸到會寫字的人也不多。
但也不知道為何,她莫名就是覺得那字迹有些熟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