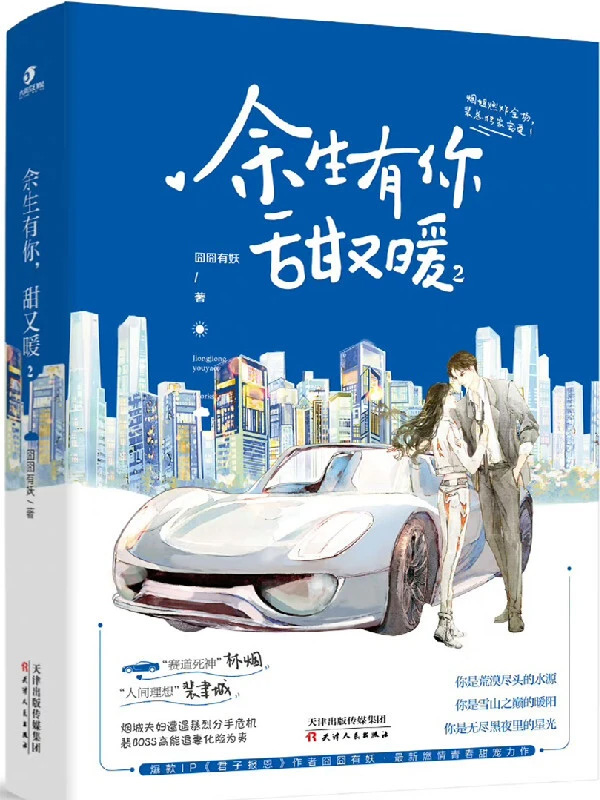第62章 執行家法
溫甯疼得閉上了眼睛,唇卻依舊閉得緊緊的。
陸晏辭被她這一副倔模樣氣得不輕。
不過,這小東西有多能忍他不是不知道,隻是從痛感上收拾她,是達不到目的。
他眯起了眼睛,眼底暗冷的戾氣越發凝重。
這小東西不僅敢到處亂跑,脾氣也不小。
人能去的地方和鬼能去的地方她根本不分,今天那種地方,魚龍混雜,如果遇到的是别人,說不定今天就被吃了,連骨頭渣子都不剩。
她一點分辨能力也沒有嗎?
不如如此,還敢當衆讓他難堪,這會又死不認錯,倔得要死。
看來不動家法是不行了。
他看看溫甯緊閉的雙眼,冷冷的開口,“這是你自找的,溫甯。”
說罷,手上用力,直接将她像抓鹌鹑那樣提起來挂在手臂上,幾步就走到了那個用來洗牛奶浴的偏房門口。
管家跟在後面,低聲道:“小三爺,溫小姐還沒吃晚飯,要不吃了再懲罰吧。”
陸晏辭手一頓,剛要把溫甯放下來,溫甯突然掙開陸晏辭的手下地就想跑。
誰料還沒跑出兩步遠,衣服領子就被陸晏辭提住了。
陸晏辭心底怒意更甚,就像提着個小幼崽一樣把她提了回來。
面色也冷得像剛從冰窟窿裡拿出來一樣,聲音帶着濃郁的怒意,“門打開!”
管家看了一眼糾纏不清的兩人,微不可見的搖了搖頭,取出鑰匙把門給打開了。
裡面是一個比較小的溫泉室,當時按照陸晏辭的要求臨時添置的,裡面東西還算齊全,就是小了一些,溫泉池裡也還沒有放水進去。
陸晏辭把溫甯提到屋裡,往休息的椅子上一放,聲音又冷又無情,“自己在這裡想錯在哪裡了,想明白了再出來!”
溫甯擡頭看了他一眼,胸口有些起伏,不是沒有動怒。
但她知道自己玩不過他,迅速的垂了下腦袋,死死的咬着唇,手也死死的握成了一個拳頭。
陸晏辭知道一時半會她絕不會軟下來,冷冷的看了她一會兒,轉身就走。
剛走到門口,溫甯軟糯的聲音就響起來,“你不能把我關在這裡。”
聽着很軟,但裡面卻含了鋼筋混凝土做的骨頭,一點服軟的意思也沒有。
陸晏辭眸底冷意更甚,頭也沒回,直接出了門。
随後,一聲悶響,門徹底合上。
這個房間雖然也是溫泉室,但畢竟是臨時添置的,并不能和那個大玻璃房相提并論。
門關上後,裡面很黑,沒有窗戶,隻有從斜上方的排氣扇那裡透進來一點光,溫甯蜷在椅子上,望着那一束光出神。
憤怒又如何,不甘心又如何,恨又如何,在他們那些人眼裡,她這種人不過就是一個玩物,一個死活都不重要的畜生。
就像那個被扔出門外的女孩,就像那個被活活踩得半死的男人。
陸晏辭是誰,京圈權勢階層的頂流,要風得風,要雨得雨,她怎麼玩得過他?
他現在對她有興趣,還當她是個金絲雀,閑了歡喜了上來投點食,要是不喜歡了,也不過是扔到看不到的地方,任人欺淩罷了。
想到那屋子裡發生的一切,原本早就麻木的心突然又被什麼拽着往外扯一樣,又悶又痛。
陸晏辭和她本就是兩個次元的人,她不該對他有一絲一毫的奢望。
她就那樣一動不動的坐着,不知道過了多久,她蜷在椅子上睡着了。
溫甯在裡面坐了多久,陸晏辭也在屋外的椅子上坐了多久。
他看着那屋子的門,看了很久,直到天氣驟變,開始起風,她也沒有來敲門,更沒有發出一點求饒的聲響。
風來得很陡,吹得樹木嘩嘩作響。
管家拿了鑰匙,走到陸晏辭面前,“小三爺,要不要打開?已經關了三四個小時了,她還沒喝藥。”
陸晏辭看着那扇烏黑的門,感覺自己所有的耐心在這一刻被磨光了,戾氣慢慢的浮上了雙眸,“一次不喝死不了,我看她能有多倔!”
管家看了看門,把鑰匙又收了起來。
這時,陸晏辭的電話響了,他拿起來看了看,接通了。
過了一會兒,他合上電話,盯着那扇門,神色很冷:“我出去一會兒,你盯着她,如果敲門認錯就放出來,不認錯就讓她一直在裡面呆着。”
“沒我的話,不準開門,不然你就自己進去呆着!”
說完,轉身就出了大廳。
管家看着緊閉的大門,面無表情的搖了搖頭,然後進了屋,拿起了手機。
“夫人,晏辭少爺的病好像又有點要發作的趨勢。”
“您過些時間要回來?”
“好!"
……
沒過多久,突然狂風大作,電閃雷鳴,暴雨傾盆而至。
溫甯蜷在椅子上,身子忍不住發顫。
周言下葬的那天,也是這個天氣。
潮濕的空氣夾着雨腥氣從排氣扇的縫隙裡擠進來,充斥着整個空間,溫甯有些恍惚,覺得這天氣都和那天都一模一樣,似乎在流血。
她從小怕打雷閃電,每次這種天氣,父親就會喝酒,醉了就把母親按在地上往死裡打,罵她為什麼生不出兒子,打完了母親就打她。
她到處躲,沒人敢收留她,隻有周言一次次向她打開門。
周言死了之後,她失去了害怕的資格。
黑暗中,她蜷成一團,想象中周言把她帶進安全的空間,想象着周言煮給她了桂花甜湯。
周言是她的光,是她的救贖,是她能抓住的唯一救命浮木。
可,這樣好的周言,被人用那樣肮髒的手段活活玩死了。
周言,她的周言,他絕不能這樣白白的死!
突然,刺眼的閃電滑過,帶來巨大的雷鳴,震得整個屋子都在發顫。
溫甯猛的睜開眼睛,看向牆上的排氣扇。
電閃雷鳴中,她仿佛聽到有人在敲門,有人在叫她的名字。
有人叫她快跑,跑得遠遠的,别讓人抓到。
她蒼白着臉,把凳子搬到排氣扇下方,用刀子撬開了那兩個連排的排氣扇。
清瘦纖薄的她,輕而易舉的鑽了出去。
外面狂風暴雨,樹木瘋狂搖擺,路燈的光線仿佛都被風吹得變了型。
她拖着濕漉漉的衣服,順着牆慢慢的向另外一邊摸過去。
剛進走廊,最外面的房門突然打開,一隻手大力的将她拽了進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