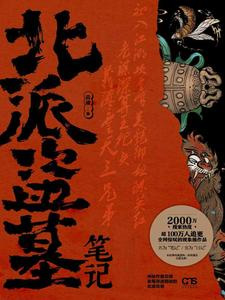不知道對方是誰!也不知道對方是怎麽跟著我們找到到了這裡!此刻我隻知道,突然襲擊我們的這人手裡有家夥事兒!
“砰砰砰!”
慌忙中,我朝窗戶那裡胡亂開了幾槍。
因為這把小槍隻能打三發,我立即藏到桌子後裝子彈。
桌子實木做的,很厚實,勉強能用來當臨時掩體,我隨身隻帶了六顆子彈,打完就沒了。
“魚哥!”
看魚哥有了反應,我大喜。
“砰!”
我伸手試了下他鼻息,還能感覺到有口氣兒。
由於過於緊張了,黑暗中我能清楚聽到自己的心跳聲和呼吸聲。
我在明,敵在暗,現在不能坐以待斃,要主動出擊才有贏的機會。
哪料到,下一秒老頭突然雙腿一蹬,脖子一歪,在沒動靜了。
我大喜,馬上用力拍他臉。
隻見剛剛還和我們侃侃而談的老頭兒王富貴,此刻靠著椅背腦袋歪到了一旁,他雙目緊閉,嘴角兒周圍有白沫殘留,像中毒了一樣。
一時間我有些暈頭轉向,感覺這些事兒毫不相乾,又感覺彼此間有關系,隻是我們還不知道。
之前我在東山石窟的牆上,無意中發現的那幅潦草簡單的壁畫,落款時間是清代末年,落款人寫的是江什麽。
“不清楚這人應該不是跟蹤我們過來的,這人可能原本就藏在村子裡,是我們到這裡後引起了他的注意。”
剛才一路開車過來,我一直有留意反光鏡,這是習慣,當時我根本沒看到有車跟在後頭。
魚哥手捏住老頭兒脖子,我便看到了一根不粗不細的“針”紮進了肉裡。
這時魚哥靠了過來,我壓低聲音道:“等一下,先別出去。”
我解釋說:“這槍便攜性高,威力差了點兒,近距離還行,遠距離就不行了。”
“對了!那老頭兒!”
緊接著我小心翼翼找到其脖子上銀針位置,用指甲蓋掐住,一點點兒將針從他脖子上抽了出來。
魚哥點頭,他掏出手機打開手電筒功能攥在手中,謹慎邁步出去了。
聽到槍響的第一時間我開門衝了出去,果真就看到一個“黑影”貓在窗台下方!我直接朝對方開了槍。
他本處在無意識的昏迷狀態,突然咳嗽了一聲,一嘴鹽噴的到處都是。
魚哥覺得我說的有道理,馬上跑去廚房找了半包鹽過來。
隻見院子裡空空如也,連個人影子也沒有。
“看來人跑了,雲峰,你那一槍應該沒傷到對方要害。”
這難道是巧合?
屋內伸手不見五指,靜可聞針。
手機一照。
我明白了他意思。
“大爺!睜開眼!快醒醒!”我大聲呼喊。
“我確定剛才有一槍打中了,魚哥,咱們兩個出去看看人死了沒,我在後頭掩護你。”
事發突然,剛剛那一槍差點要了命,所以魚哥臉上也顯的有些驚魂未定,他喘著氣小聲問我:“雲峰,這人是誰?他怎麽知道我們要來這裡?又是怎麽跟著我們到這裡的?”
地上有個盛水用的皮桶,魚哥看了我這裡一眼,抓起來水桶猛的砸了過去。
我由於常年下墓的原因,勉強還能看清周遭環境。
伴隨著槍聲和燈泡的炸裂聲,周遭瞬間陷入了黑暗。
很快我手摸到了門把手。
或者說蘊藏著某些不為人知的秘密?
之前我和查叔被人做了暗殺局差點橫死街頭,會不會也和這條線索有關?
到了窗戶那兒,隻見地上有一小灘血跡,我兩又出去大門口,繞著房子周圍找了一圈,沒發現人。
“這是.吹針??”
於是我緊貼牆壁,貓著腰掂起腳尖,一步步摸了過去。
我接過來沒猶豫,用手捏住老頭兒下頜,直接往他嘴裡倒了半包鹽。
壓好子彈後我擡頭瞄準天花闆,豪不猶豫扣動了扳機。
千島湖.水下古城方臘寶藏薛坑口.踏地先生壓地姑.摩尼教.夏家江姓這些之間到底存在著什麽關系。
等了幾分鍾,聽外頭沒什麽動靜,我側著身子,慢慢探頭向外偷瞄。
魚哥眉頭緊鎖,點頭:“是吹針,八成是道上人,對方不想讓我們從這老頭口中知道某個秘密,所以才下了手,要不是我提前察覺到了,你我可能都會不明不白死在這屋裡。”
情況緊急,我急道: “這辦法我是以前在精神病院的時候聽一個人說的!我忘了那人叫什麽了!”
我 回過神來,趕忙跑回家中。
現在槍裡剩最後一顆子彈,我不敢亂用。
我則舉槍緊跟在他身後掩護他。
魚哥立即摸了摸他脈搏,臉色很難看道:“不妙,人死了.”
老頭兒馬上有了反應。
“眼下出了村都是土路!路不好走!這三根半夜,離醫院好幾十公裡遠!我怕送過去來不及了啊!反正試試怕什麽!就拿死馬當活馬醫!這老頭兒堪稱江湖活化石!他指不定還知道什麽大秘密!要不然怎麽咱們一來就有人暗殺他滅口!”
我正考慮要不要把人送醫院,這大半夜該去哪個醫院,到醫院了又該怎麽說,這時忽聽魚哥講: “雲峰你看這裡,咱們剛剛沒注意到,原來是這東西害的。”
“魚哥,你趕緊去廚房找找看有沒有鹽,我聽人說,凡是中了吹針的人,隻要嘴裡含口鹽就能醒過來!”
從開門到開槍,整個過程撐死兩秒鍾,等對方反應過來,我又迅速躲到了門後。
“你聽誰說的?還有這種說法?要是想救人咱們應該趕快送醫院。”
這讓我聯想到了一幕。
我暗自心驚,因為魚哥察覺到了,所以對方慌亂下才開了槍。吹針是過去一種暗器,現在很少有人用,如今可能隻在博物館中能看到實物了,一般都是細竹子做的,用的熟練的人或者肺活量大的人,能輕松把針吹到五十米開外的地方,堪稱殺人於無聲無息,而這種針大概率要麽是毒針,要麽是麻醉針。
下一秒魚哥一個翻滾滾了過來 ,隻見他眉角被流彈擦破,流了不少血。
剛剛這老頭最後說了一個字,“江”。
顧不上擦血,魚哥立即衝我比了個手勢。
我臉色更加難看!
怎麽會這樣?精神病院的人教我的辦法似乎沒用,甚至起了反作用,針一拔出來人直接沒了!
魚哥此刻警惕打量周圍,看向我問:“咱們現在怎麽辦?”
突然出了這種岔子誰也沒料到, 我想了想,咬牙道:“咱們趕緊回去,找把頭!”(本章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