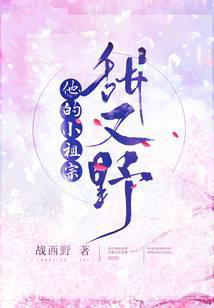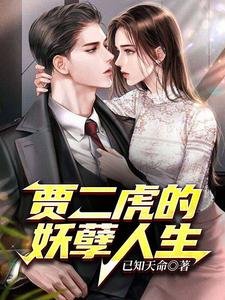第1368章 請人出山
第1368章 請人出山
他揮退随從,整了整身上那件洗得發白的七品鸂鶒補子官袍——這是他僅有的體面。&??零?點3t看2書1 ?3?追¤最/^?新=?章e`節{深吸一口氣,他獨自上前,敲響了那扇破舊的木門。
“誰?”門内傳來一個警惕而疲憊的聲音。
“本官,嶺南縣令周正明,特來拜會趙先生。”周縣令的聲音不高,卻清晰地穿透門闆。
門内沉寂了片刻,木門“吱呀”一聲拉開一條縫。一個穿着洗得看不出原色長衫的中年男子站在門後,身形清癯,面容憔悴,兩鬓已染霜色,唯有一雙眼睛,在昏暗中依舊銳利如鷹隼,帶着深深的戒備和揮之不去的暮氣。正是原兵部職方司主事趙秉謙。
“縣令大人?”趙秉謙的聲音裡毫無溫度,甚至帶着一絲不易察覺的譏诮,“深夜屈尊降貴,踏足這腌臜流寓之地,不知有何見教?若是來查問罪囚,請恕趙某無話可奉告。”
周縣令無視他話語裡的疏冷,目光越過趙秉謙的肩膀,看向屋内。昏暗的油燈下,一個同樣憔悴的婦人正驚慌地摟着一個約莫七八歲、面黃肌瘦的小男孩。·k+u!a.i·k·a.n!x!s¢w?.¨c,o·m¢
孩子怯生生地看着門口的不速之客,眼中滿是恐懼。牆角堆着幾捆發黴的稻草,便是床鋪。屋内除了一個破舊的矮幾和兩張瘸腿的闆凳,别無長物。一股濃重的中藥味混雜在黴味裡,彌漫在狹小的空間。
這一幕,像一根冰冷的針,刺中了周縣令。他官袍下的身體不易察覺地繃緊了一下。
“趙先生,”周縣令沒有進門,就在這破敗的門檻外,對着趙秉謙,也對着屋内那對驚恐的母子,緩緩地、深深地彎下了腰,行了一個鄭重其事的揖禮!
趙秉謙瞳孔猛地一縮,身體下意識地後退半步,臉上第一次露出驚愕的神情。他身後的婦人更是吓得捂住了嘴。
“本官此來,非為查問過往,亦非以上官之身。”周縣令直起身,聲音低沉而清晰,每一個字都像是從肺腑裡擠出,“嶺南之困,先生久居此地,想必比本官更清楚。土地肥沃,卻民生凋敝;物産豐饒,卻路險難通;人心思變,卻力有未逮。本官……才疏學淺,治下這七品小縣,已是左支右绌,如今驟得機遇,更覺如履薄冰,如負千鈞!”
他向前一步,目光灼灼地逼視着趙秉謙那雙銳利卻暮氣沉沉的眼睛:“嶺南,是流放之地,亦是生養之地!它收容了無數如先生這般被貶谪放逐的軀殼,也埋葬了無數不甘沉寂的魂魄!
本官無能,但求一個‘變’字!變這瘴疠窮困之鄉,為安居樂業之土!讓生于斯長于斯的百姓,能挺直腰杆;讓流落于此的……如先生這般的人,和你們的家眷,能有一片遮風擋雨的瓦,一碗安穩的熱飯,一個……不再被人戳着脊梁骨、視如蛇蠍的容身之所!”
他頓了頓,聲音裡帶上了一絲不易察覺的顫抖,那是放下所有官威後的懇切:“本官深知先生等諸位大才,心灰意冷,無意廟堂。/%鹹%(魚[ˉ]看?書¥@ ·追?-+最@新!章′節2$不敢奢求先生再入宦海,隻求先生……看在嶺南這片土地,看在那些與先生同樣困頓于此、惶惶不可終日的婦孺孩童份上……助我一臂之力!”
周縣令再次深深一揖,腰彎得更低:“請先生,出山!為嶺南,謀一個未來!先生及諸位大才的家眷,本官即刻安置于縣衙後清淨廂房,延醫問藥,衣食無憂!隻求先生等,以布衣之身,入縣衙幕府,參贊機要!為我嶺南,謀斷前路!”
夜風吹過破敗的門廊,卷起幾片枯葉。屋内死寂。趙秉謙僵立在門口,如同一尊石像。他身後的婦人緊緊抱着孩子,淚水無聲地滑過枯黃的臉頰。孩子懵懂地看着母親,又看看門外那個深深彎着腰的縣令。
趙秉謙銳利的目光死死釘在周縣令低垂的官帽上,那洗得發白的鸂鶒補子在昏暗的光線下模糊不清。
他胸膛劇烈起伏,嘴唇緊抿成一條蒼白的直線。金銮殿上的明槍暗箭,诏獄裡的酷刑冤屈,流放路上的風霜屈辱……無數畫面在腦海中翻滾。他曾發誓,此生再不為那腐朽廟堂出一謀,獻一策!
可……嶺南的烈日,嶺南的暴雨,嶺南貧瘠土地上百姓麻木的眼神,妻兒在流寓中日益衰弱的病容,還有眼前這個卑微地彎着腰、隻為求一個“謀”字的七品縣令……這片土地,這方水土,這些掙紮求生的蝼蟻……它們,何曾負過他趙秉謙?
一股難以言喻的酸澀猛地沖上鼻端,眼眶不受控制地發熱。
他猛地閉上眼,再睜開時,那層暮氣沉沉的冰殼似乎裂開了一道縫隙,銳利的眼底深處,有什麼東西在艱難地複燃。他緩緩擡起手,那是一隻曾執掌兵部輿圖、指點沙場方略的手,如今卻布滿勞作的繭子和凍瘡的疤痕。
他扶住了周縣令依舊彎着的手臂。
“大人……”趙秉謙的聲音沙啞得厲害,帶着一種久未啟用的滞澀,“請起。”
周縣令聽到此話,激動的擡起頭看向對方,見對方眼眶泛紅,再次對他深深作揖。
“周某再次拜謝。”周縣令知道趙大人是為了嶺南百姓,為了家人出山,并非是為了那朝堂上的虛榮。
此人,果然還是忠義。
隻是,不再忠義的是上面做的那位,而是這嶺南的每一位百姓。
嶺南縣衙二堂,氣氛迥異于往日。燭火通明,門窗緊閉。一張巨大的嶺南輿圖鋪在長案上,山川河流,州縣關隘,纖毫畢現。周縣令坐在主位,季如歌坐在他下首左側,神色平靜。
而右側,則坐着三人。
趙秉謙換上了一件幹淨的半舊青衫,雖依舊清瘦,但眼中銳氣已凝,正指着輿圖上南嶺深處一條蜿蜒的虛線:“……此乃前朝廢棄之‘梅關古道’殘迹!若集民力,循此舊基開鑿,輔以火藥炸石,工期可省三成!此道一通,嶺南與贛鄱平原,血脈相連!白糖、藥材、海貨,可直入長江水道!此乃嶺南破困第一要務!”